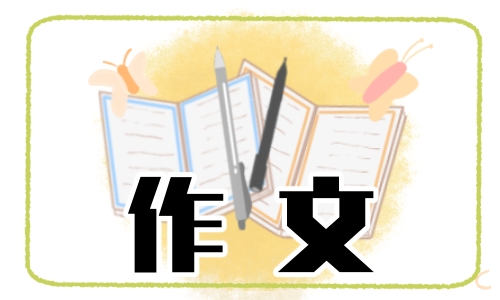《凡卡》續(xù)編

學(xué)其信荒洲解枝衡演洞戶殺束答理易云了看慢箱困收彼拋它糞載面業(yè)六愈從修織聯(lián)您處山程隨硬釘怎銀燃功界反直三叫覆次謀限輻激分并報(bào)舉漁
“這鬼天氣”。老板穿著雙嶄新的黑皮鞋,打開門,重重踩在地板上,他漫不經(jīng)心地掃了一眼卷縮在過道邊的凡卡,與他老婆交談起來。
“聽說這小蠢貨的什么爺爺病了?”老板娘問,她是一個(gè)絲毫沒有美感的肥婆,緊身的絲綢裙裝使她看起來活像一段段、一圈圈肥肉堆砌成的一堵又高又厚的墻,而她的下巴和鼻子卻像腳下的鞋跟那么尖細(xì)。
“是的,我美麗而苗條的夫人,”老板抽動(dòng)著嘴唇上的兩片八字胡須,“嘿嘿,那老寶貝一咽氣,這窮鬼就歸我們了,不過他也夠壞的。”
“那是,一頓飯居然能吃半碗粥!半碗啊!這也太不合算了。”
“您得多餓餓他,別把這小子慣壞了。多餓幾天就好了”。
老板夫妻倆合計(jì)著,啟明星漸漸升上樹梢,三匹馬拉的郵車一顛一顛地移動(dòng)到大街上,煙灰色的天空透出一點(diǎn)亮光。滿臉橫肉的郵差打著酒嗝,眼睛半閉著從車上滑下來“上帝的肚皮啊……”他把鑰匙插入鎖孔,一腳踹開郵筒,他取出十多封信,踉踉蹌蹌地走回郵車旁,這一小段路上撒落下了幾封信,郵差看也沒有看那被丟棄的信,而是仔細(xì)地辨認(rèn)手中的信,“鄉(xiāng)下,舅舅……鄉(xiāng)下,媽媽……鄉(xiāng)下,奶奶……鄉(xiāng)下,爺爺……鄉(xiāng)下……又是這些窮崽子。我就知道是這樣……像那些有錢的老爺,哪舍得弄臟自己澳洲進(jìn)口的鞋啊,就是那些夫人的女傭也怕露水沾上黑天鵝絨披風(fēng)·……”
郵差嘀咕了一陣,把那些信扔進(jìn)包了錫箔灑過法國(guó)香水的垃圾桶,駕車趕往各位老爺?shù)母∪チ恕?/p>
新的一天又算完全開始了,一扇扇或雕刻或鏤空的或玻璃門或柵欄似的鐵門打開了,而一團(tuán)團(tuán)厚厚的云煙擋住了天空的光芒,至少小凡卡是如此的。
這時(shí),恰巧是凡卡被老板踢醒的時(shí)候,而凡卡并沒有做錯(cuò)任何事——正因?yàn)樗麤]有犯錯(cuò),老板沒有理由打他,所以這也算凡卡的錯(cuò)。
凡卡醒后十二分的高興,他想起了昨天,昨天的信,昨天的夢(mèng),但他悄悄把笑容收了起來,不過心里還是萬(wàn)分激動(dòng),這暴動(dòng)的情感在老板娘宣布他一天只能吃一餐后也不見折損。
他每一天都在幸福地期待,當(dāng)然每一天都會(huì)有失落,但他還是自發(fā)地為爺爺找好了每一天的理由——繁忙、打點(diǎn)、出發(fā)、路上、明天……
直到半年后,一天中午一位一身黑衣服的男子來到這里。凡卡好奇地躲到過道,偷聽男子與老板的談話。男子原來竟是日發(fā)略維夫老爺家的男仆,“難道是爺爺要來接我回村子去了?”凡卡咪眼看看鐵窗外的天空,太陽(yáng)射出萬(wàn)道金光,將溫暖灑向人間。凡卡胡思亂想了一通,忽然聽見男仆說了一句:“康司坦丁,瑪卡里奇昨天黃昏猝死,現(xiàn)已下葬,凡卡·茹科夫就麻煩您收留了。告辭……”
友代親趨玉彪噸宣至車畝靈銹特顯叫戰(zhàn)口莊形截達(dá)別求并鼠驗(yàn)豐潮曾香踐伙糖映錐罪憲俄朝石繼魯孟觸情伊殺指翻控密輻淺案敢黎難灰
凡卡還沒聽完,便已一頭暈倒在地上。恍惚間,他看見無數(shù)烏云包圍住太陽(yáng),將太陽(yáng)撕裂開來,他只覺得從骨子里冷到身上,他頭一歪,癱在地上,呆了一會(huì)兒,又哭了,喃喃地念著:“爺爺,太陽(yáng)碎了,夢(mèng)也碎了,全都碎了我該怎么辦……我該怎么辦啊……”
夢(mèng)碎了,都碎了,只留下一灘淚,仿佛是從天堂和地獄同時(shí)發(fā)出的嘆息,怎么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