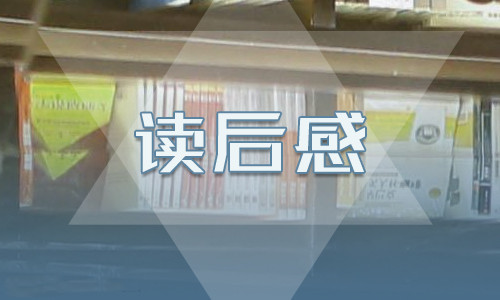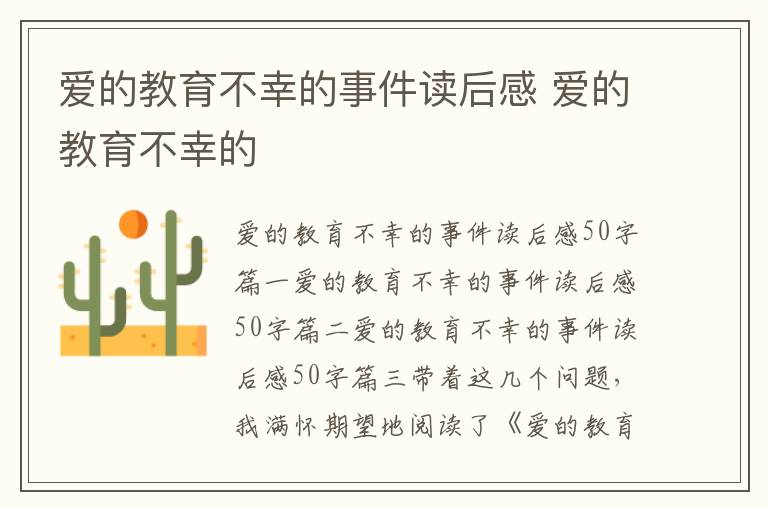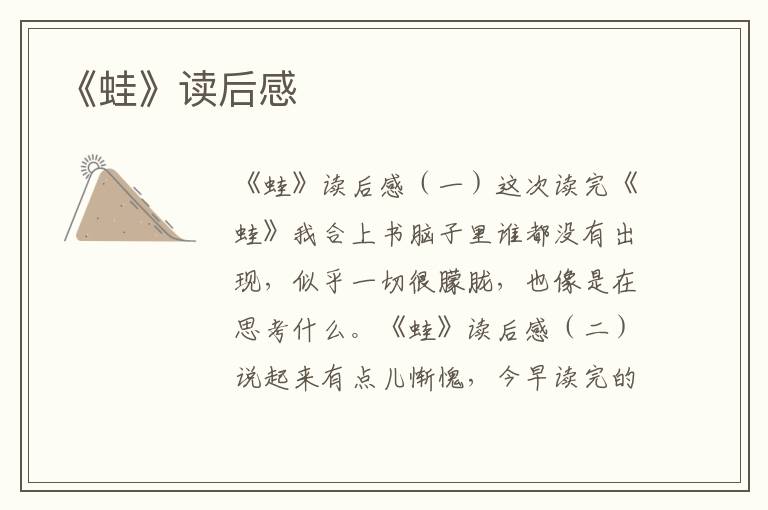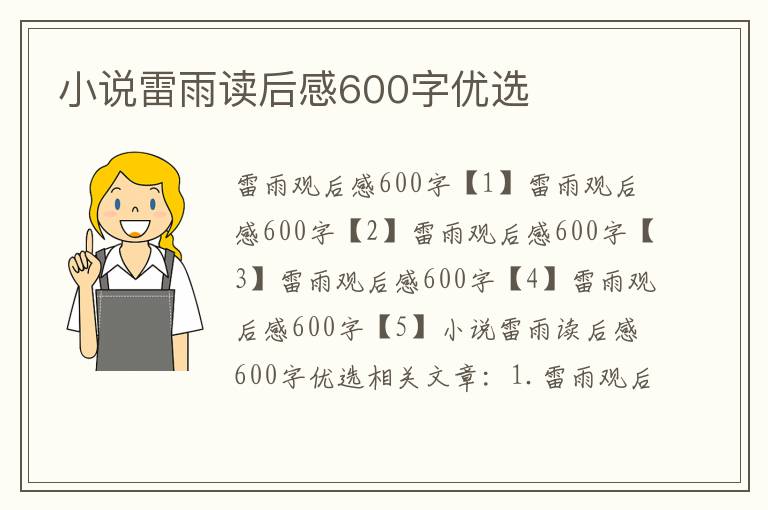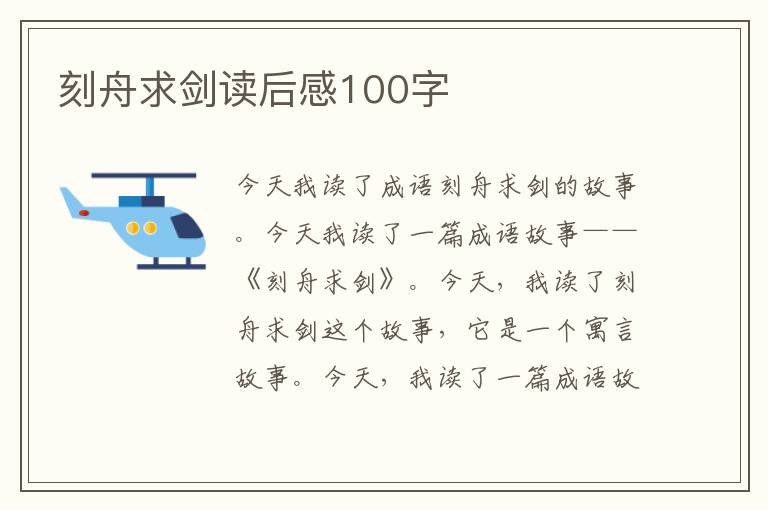2023年3月《詩(shī)刊》讀后感丨楊碧薇

原標(biāo)題:2023年3月《詩(shī)刊》讀后感丨楊碧薇
文丨魯迅文學(xué)院教師 楊碧薇
一轉(zhuǎn)眼,2023年的春節(jié)已經(jīng)過(guò)去,春天重回大地,草長(zhǎng)鶯飛。又是三月好時(shí)節(jié),2023年第三期《詩(shī)刊》也如約飛到我手上,為我打開(kāi)了一個(gè)精彩紛呈的詩(shī)歌世界,讓我再次感受到漢語(yǔ)熱氣騰騰的生命力。
在上半月刊的“讀詩(shī)”欄目,王家新的一首《黎明》,用飽蘸著時(shí)間性的儀式感,徐徐地揭開(kāi)了三月的帷幕。這首詩(shī)既有視角的對(duì)位,又有角色的移情;人的主體意志投射到動(dòng)物身上,詩(shī)歌意義的建構(gòu)便具有了雙重性。用王家銘的話來(lái)說(shuō),這就是“生命的互相發(fā)現(xiàn)”。
在“視點(diǎn)”和“新時(shí)代”欄目,王太貴的《扶貧手冊(cè)上的紅手印》、謝子清的《第一書記》都是扶貧題材的詩(shī)歌。“精準(zhǔn)扶貧”以不同于以往的社會(huì)/歷史實(shí)踐,更新了詩(shī)人們的國(guó)家/個(gè)體經(jīng)驗(yàn)。在這些詩(shī)里,我看到一種迫切的敘事性,它恰好說(shuō)明了時(shí)代對(duì)詩(shī)人和語(yǔ)體的雙重沖擊。正如王太貴寫“那種甜啊,在心中久久縈繞”,“精準(zhǔn)扶貧”對(duì)當(dāng)代漢詩(shī)乃至整個(gè)當(dāng)代文學(xué)的影響,都將會(huì)持續(xù)下去。
“方陣”中,杜涯的組詩(shī)《發(fā)生》保持了其一貫的水準(zhǔn),但她并不滿足于此。她對(duì)世界的體認(rèn)和對(duì)詩(shī)歌的追求,都“繼續(xù)走在成長(zhǎng)之路上”。以詩(shī)為價(jià)值建構(gòu)的橋梁,她指出了一個(gè)方向:“整體,是我們終究要回去的地方”。趙野的《你的花園》有著迷人的“趙野式語(yǔ)體”,展示了一種清晰的漢詩(shī)發(fā)展方向:古典即現(xiàn)代。在傳統(tǒng)與當(dāng)代的承續(xù)中,詩(shī)與個(gè)體都將獲得救贖,“我們終究會(huì)消散啊”,但“浮生暫寄,一笑就成春意”。劍男的組詩(shī)《漣漪》依托于生動(dòng)的場(chǎng)景性,讓思緒的漣漪疏密有致地泛起,日常場(chǎng)景與詩(shī)思相互啟發(fā),展現(xiàn)出及物與超越性兼得的詩(shī)意路徑。
池凌云的這組《山中書簡(jiǎn)》再一次證明了她“上天入地”的能力。所謂“上天”,就是她的詩(shī)一直保持著對(duì)形而上的終極問(wèn)題的關(guān)注,如火燒云讓她感受到的是“無(wú)垠宇宙遞送過(guò)來(lái)的/閃耀之物”;“入地”則指她在看待世間萬(wàn)象時(shí)的悲憫與同情,如《落入凡間》將普通勞動(dòng)者進(jìn)行圣化處理,讓我們看到這些“隱身在人群中的神”身上的寶貴品質(zhì)。藍(lán)藍(lán)的一組《水井》從兒童視角看人間悲歡,讓人想到林海音的《城南舊事》。與《城南舊事》寫城市生活有所不同《水井》彌漫著干凈的鄉(xiāng)野氣息。同時(shí),這組詩(shī)使用了更簡(jiǎn)潔的句式,凸顯出作者返璞歸真的詩(shī)藝追求。施施然的組詩(shī)《雨中》,外有散點(diǎn)式的地理坐標(biāo),內(nèi)有持續(xù)集中的內(nèi)心發(fā)現(xiàn),透露出更替與延續(xù)的時(shí)間觀:“有些事物消失了/而新的事物正在形成”;同時(shí),詩(shī)里也充盈著美的細(xì)節(jié):“青瓷蓋碗的裂隙中,龍井混合茉莉/斜斜地溢出微溫香氣”。
在“氣象”欄目,張煒的《南部山區(qū)》用記述性的手法描繪了一幅南部風(fēng)物畫,這個(gè)有著“所有的隱秘”的世界,像是另外的時(shí)空,亦像一部小說(shuō)的背景。全詩(shī)在從容的敘述中隱約透露出一種元文化(meta-culture)的風(fēng)味。而在本期“每月詩(shī)星”中,批評(píng)家胡亮貢獻(xiàn)出一組奇妙的小詩(shī)。“夜色的手掌,提攜了我的青枝”、“兩爿柔性剪刀的扺掌談”……一詞一言,皆充滿智趣。胡亮的詩(shī)似隨手抓取,詩(shī)思爛漫,有一種難得的自在狀態(tài);所謂舉重若輕,正是深厚的詩(shī)學(xué)素養(yǎng)賦予他這種奇力。
本期“國(guó)際詩(shī)壇”刊載的是伊朗女詩(shī)人葛拉娜茲·穆薩維的作品,正如總標(biāo)題《被禁止的女人之歌》所示,身份問(wèn)題是這組詩(shī)的核心概念之一。“我”的自我表達(dá)對(duì)照于“你”這一參照系,“我”必須通過(guò)自闡、辯證向“你”(他者)論證“我”的情感、想法和立場(chǎng)。“我”是“一個(gè)奇怪的女人在你的夢(mèng)中被闡釋”,暗示了身份建構(gòu)的困境。“短歌”中,蔡小華的《騎樓老街》、王長(zhǎng)征的《在雙橋》依托于特定的坐標(biāo),把人之情與意加予騎樓和雙橋,再次在新詩(shī)中激活了古典漢詩(shī)的寄情方式。
在下半月刊的“雙子星座”中,曉角的組詩(shī)《外婆》從個(gè)體出發(fā),緊貼個(gè)人生活,充滿真情實(shí)感。“春天是個(gè)好孩子/他穿著粗布衣服/他很勤儉”,表述簡(jiǎn)潔有力,并讓人相信,它與詩(shī)人的心同步。而詩(shī)歌的感染力,往往正包蘊(yùn)于干凈樸素的言說(shuō)之中。這組詩(shī)里,值得一提的是《一塊潤(rùn)膚油》,詩(shī)人從潤(rùn)膚油想到“正如一段糖/雪落到本質(zhì)應(yīng)該也是這樣”,這種物感方式讓人眼前一亮。
“銀河”欄目里,嚴(yán)彬的《我爺爺和我爸爸的枇杷樹(shù)》《微風(fēng)輕拂的時(shí)候……》等詩(shī)暗套了小說(shuō)/民間故事的講述方式,借用了故事之魂,語(yǔ)言也滲透出敘事文體的味道。《我為什么喜歡看云》的寫法也很獨(dú)特,前三段讓人想到議論文里的舉證,第四段轉(zhuǎn)而寫“我們熟悉的流浪漢”。注意,“我們”一詞巧妙地隱含了一個(gè)敘述者(說(shuō)書人),TA既是故事的講述者又是詩(shī)意的撬動(dòng)者。流浪漢的故事讓我想到卡爾維諾小說(shuō)里那些“離去—?dú)w來(lái)”的人。詩(shī)歌的末尾,流浪漢成了一名詩(shī)人,在全詩(shī)的語(yǔ)境下,這個(gè)安排令人信服,實(shí)際上它也回答了為什么喜歡看云的問(wèn)題。另一位詩(shī)人麥豆,則在組詩(shī)里繼續(xù)著他“生活觀察家”的態(tài)度。麥豆喜歡察物,并常常有新鮮的感受。《小雨》中他寫雨中的鳥(niǎo)“像一塊石頭/停在樹(shù)上”;《下雪了》中寫“天空晦暗/但我們贊美它/孕育了一場(chǎng)雪”;寫到房子,他也會(huì)注意到“三樓是空的。/一樓住著一位老人/去年,曾是兩位。”他的詩(shī)印證了詩(shī)歌中的新感受力(桑塔格語(yǔ)),讓我們對(duì)新詩(shī)的感受能力報(bào)以期待。精妙的物感,在黃勝的《銅錢草》中也生動(dòng)地存在。銅錢草的形狀“讓人聯(lián)想金幣、大洋/錢莊的算珠”,這還不夠,詩(shī)人啟用了通感,聽(tīng)到了“金石般鳴響……蕩漾的聲線……檐下風(fēng)鈴”。通感豐富了詩(shī)意的層次,《銅錢草》當(dāng)為黃勝這組詩(shī)中最別致的一首。
李長(zhǎng)瑜的組詩(shī)《堅(jiān)果》也頗見(jiàn)功力。以《致》為例,詩(shī)歌寫得飽滿但又沒(méi)有過(guò)重的痕跡,在敘述接近飽溢之時(shí),詩(shī)人知道要及時(shí)地騰挪跳閃,給想象和句子都留出空間。王馨梓的《他回來(lái)了》抓住了一個(gè)具體的場(chǎng)景,呈現(xiàn)出迷人的敘事性;另一首《驕傲猝不及防》展示了詩(shī)人在現(xiàn)實(shí)中的某種困境,詩(shī)歌第二段將視點(diǎn)從個(gè)體轉(zhuǎn)移到香樟樹(shù)上,與第一段中的人之困境暗暗扣合,“地上有多少枯葉,枝頭就有多少嫩芽/昨夜未見(jiàn)雷霆,蛻變無(wú)聲無(wú)息”實(shí)乃佳句。蔣興剛的這組詩(shī)勁道醇熟,他已有了屬于自己的寫作路徑,一首詩(shī)只要一發(fā)動(dòng),他就能輕車熟路地開(kāi)下去。但有時(shí)候,“熟”對(duì)詩(shī)歌來(lái)說(shuō)不一定是好事,蔣興剛知道這一點(diǎn),知道詩(shī)也需要“從未經(jīng)歷的/下一秒”,因此,他在詩(shī)里留出意外,“我目視空枝,把消逝變成了可見(jiàn)之物”。
“校園”欄目一直追蹤校園詩(shī)歌的腳步,體現(xiàn)了《詩(shī)刊》關(guān)注新人、助推新詩(shī)發(fā)展的一面。本期“校園”里,吳任幾的《回歸年》采用了靈活的敘事方法,其中有電影式的鏡頭特寫,“雨水順著杉木淌下樹(shù)根”,有意識(shí)流、場(chǎng)景描繪、議論和插敘,搭建起一種成熟的敘事形態(tài),整首詩(shī)閃耀著精彩的表現(xiàn)力。王彤樂(lè)的《長(zhǎng)夏記事》有著清晰的美學(xué)走向,藍(lán)色、信件、老街、紙船、琴鍵等物事無(wú)一不傳遞著“舊”的美學(xué)態(tài)度。全詩(shī)像一部文藝片,也說(shuō)明懷舊在詩(shī)意里始終有著巨大的市場(chǎng)。
總的來(lái)說(shuō),第三期《詩(shī)刊》猶如當(dāng)代漢詩(shī)的一份微縮景觀,透過(guò)它,我看到當(dāng)代漢詩(shī)不同的側(cè)面、梯隊(duì)和生態(tài)。在“后疫情時(shí)代”,人類其實(shí)正站在新的歷史節(jié)點(diǎn)上,通過(guò)詩(shī)歌折射時(shí)代之變、描制新的時(shí)代景觀,并在對(duì)時(shí)代與靈魂的雙向叩問(wèn)中探尋漢詩(shī)的突破路徑,是我們應(yīng)盡的寫作職責(zé)。我相信,在這一進(jìn)程中,詩(shī)歌不會(huì)辜負(fù)每一顆真誠(chéng)的心靈。我更期待,人與詩(shī)組成的新的“人—詩(shī)共同體”,將作為一種新型的歷史裝置、一種有力的價(jià)值形態(tài),參與到歷史的發(fā)言和語(yǔ)言的生長(zhǎng)中。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責(zé)任編輯:
[推薦]如果您有信息流廣告需求信息流https:///河北雕瓏科技信息流廣告有限公司是一家專業(yè)以信息流廣告投放與托管專業(yè)營(yíng)銷公司,歡迎前來(lái)咨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