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齋志異三生白話文翻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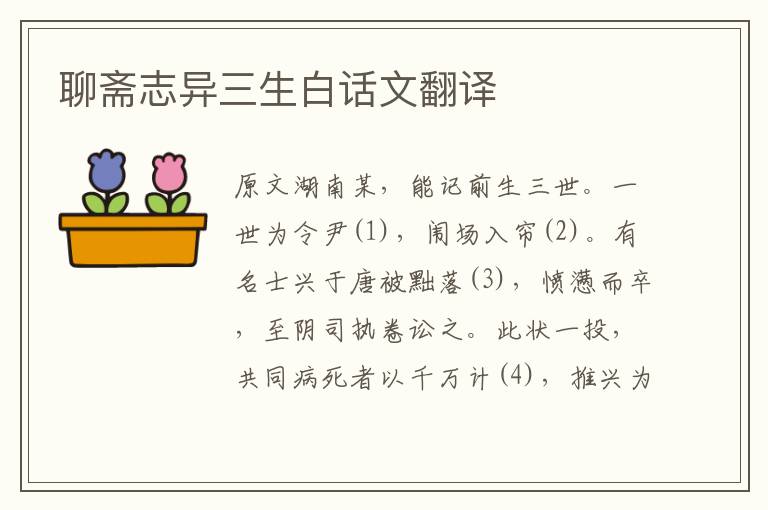
原文
湖南某,能記前生三世。一世為令尹(1),闈場入簾(2)。有名士興于唐被黜落(3),憤懣而卒,至陰司執卷訟之。此狀一投,共同病死者以千萬計(4),推興為首,聚散成群。某被攝去,相與對質。閻王便問:“某既衡文(5),何得黜佳士而進凡庸?”某辨言:“上有總裁(6),某不過奉行之耳。”閻羅即發一簽,往拘主司。久之,勾至。閻羅即述某言。主司曰:“某不過總其大成;雖有佳章,而房官不薦(7),吾何由而見之也?”閻羅曰:“此不得相諉(8),其失職均也,例合笞(9)。”方將施刑,興不滿志,戛然大號(10);兩墀諸鬼,萬聲鳴和。閻羅問故,興抗言曰(11):“笞罪太輕,是必掘其雙睛,以為不識文之報。”閻羅不肯,眾呼益厲。閻羅曰:“彼非不欲得佳文,特其所見鄙耳。”眾又請剖其心。閻羅不得已,使人褫去袍服,以白刃劙胸(12),兩人瀝血鳴嘶。眾始大快,皆曰:“吾輩抑郁泉下,未有能一伸此氣者;今得興先生,怨氣都消矣。”哄然遂散。
某受剖已,押投陜西為庶人子。年二十余,值土寇大作,陷入賊中。有兵巡道往平賊(13),俘擄甚眾,某亦在中。心猶自揣非賊,冀可辨釋。及見堂上官,亦年二十余,細視,乃興生也。驚曰:“吾合盡矣!”既而俘者盡釋,惟某后至,不容置辨,竟斬之。某至陰司投狀訟興。閻羅不即拘,待其祿盡(14)。遲之三十年,興始至,面質之。興以草菅人命(15),罰作畜。稽某所為,曾撻其父母,其罪維均。某恐來生再報,請為大畜。閻羅判為大犬,興為小犬。
某生于北順天府市肆中(16)。一日,臥街頭,有客自南中來,攜金毛犬(17),大如貍。某視之,興也。心易其小,龁之。小犬咬其喉下,系綴如鈴;大犬擺撲嗥竄。市人解之不得,俄頃俱斃。并至冥司,互有爭論。閻羅曰:“冤冤相報,何時可已?令為若解之。”乃判興來世為某婿。某生慶云(18),二十八舉于鄉(19)。生一女,嫻靜娟好,世族爭委禽焉(20)。某皆弗許。偶過臨郡(21),值學使發落諸生(22),其第一卷李姓——實興也。遂挽至旅舍,優厚之。問其家,適無偶,遂訂姻好。人皆謂某憐才,而不知有夙因也(23)。 既而娶女去,相得甚歡。然婿恃才輒侮翁,恒隔歲不一至其門。翁亦耐之。后婿中歲淹蹇(24),苦不得售(25),翁為百計營謀,始得志于名場(26)。由此和好如父子焉。
異史氏曰:“一被黜而三世不解,怨毒之甚至此哉(27)!閻羅之調停固善;然墀下千萬眾,如此紛紛,勿亦天下之愛婿,皆冥中之悲鳴號動者耶(28)?”
翻譯
湖南省的某人,能記憶前生三世的事情。
頭一世他作知縣,做鄉試的同考官。在負責閱卷工作的時候,一位叫興于唐的名士被他除名落榜。興于唐含著悲憤死去了,來到陰曹地府,拿著他的試卷訴訟某人。訴訟一經投遞,便引起數千名因同病而死的冤鬼們的共鳴,他們共同推舉興于唐作他們的首領,時聚時散,結隊成群,齊聲喊冤。陰司便把某人拘去與興于唐等人對質。閻王問:“你既然負責試卷的評審工作,為什么要貶黜優秀 人才,而選取那些平庸之輩?”某人辯解說:“我上面有負責裁決的主考官,我只不過是執行他的意圖罷了。”閻王立即發出一支簽令,去揖捕主考官。過了好久,主考官被抓到。閻王向他轉述了某人的辯詞。主考官卻說:“我不過總其大成而已;下面雖有好文章,但分管的房考官不推薦,我又怎么能看得見呢?”閻王判決說:“這件事你們不能互相推諉,失職的責任各有一半,按照律例應受鞭笞之刑。”差役們剛要對他倆施刑的時候,興于唐因嫌刑罰太輕,很不滿意,便突然大聲喊叫,臺階兩邊的群鬼一齊呼應。閻王問他們為什么喊叫,興于唐高聲抗拒說:“笞刑太輕,必須挖去他們的雙眼,作為對他們不辨文章優劣的報應。”閻王認為他們的要求太過分,不肯答應,可是群鬼的呼聲越來越高。閻王解釋說:“他們并不是不想選到好文章,只是因為他們見解太淺陋。”眾鬼便要求挖出他們的心肝。閻王不得已,只好答應他們。讓行刑的人剝去他們的袍服,用雪亮的刀子,剖開他們的胸膛,倆人鮮血淋漓,不住地叫喊。眾鬼們齊聲稱快,都說:“我們這一幫人在九泉之下受屈,從來沒有人給我們出這口惡氣;今 天幸虧有興先生,我們的冤枉終于昭雪了。”于是群鬼便一哄而散。
某人受了剖刑之后,被押送到陜西一個平民家里投生。當他二十多歲的時候,正值地方上土匪作亂,不幸陷落在賊寇之中。官府派兵巡道前來圍剿,抓捕了很多俘虜,某人也在其中。他自己在心中揣磨:我又不是賊寇,提審的時候總可以辯解清楚。當他被押到大堂上一看,坐在上面審案的縣官,也是二十多歲。再仔細打量,正是前世的冤家興于唐。便吃了一驚,心里說:“這一下,我可要完了。”果然,被俘的人員全部獲釋,只有某人留在最后發落。結果是不容置辯,竟然被斬首示眾。某人死后,來到陰曹地府,向閻王投狀訴訟興于唐。但是閻王并不立即下令拘捕,等著他享盡了俸祿的運數。一直推遲了三十年,興于唐才被揖捕歸案,與某人當面對質。興于唐以隨意殺人的罪名被罰作畜牲,又經查證某人曾經鞭打過興于唐的父母,二人判的罪應該均等。某人恐怕興于唐來生再進行報復,自己請求轉生為大狗,而興于唐則判生為小狗。
某人轉生為大狗以后,經常在順天府的街市上覓食。有一天,大狗正在街上趴著,有位從南方來的客商,攜帶一只金毛色的小狗從這里經過,形體跟一只小貓差不多。大狗審視了一下這只小狗,認出來這原來是興于唐變的。大狗認為對方體態那么小,容易對付,躥過去就咬。那小狗毫不示弱,一下子就咬住了大狗的喉管,像鈴鐺一樣綴在大狗的脖子上;急得大狗搖頭擺尾,又竄又叫。街亡的人無論如何,也不能把他們分開,頃刻之間,兩條狗同時喪命。兩狗死后,一齊來到陰司衙門找閻王評理。他們各持一端,爭論不休。閻王說:“你們兩個這樣以冤報冤,何時算完?今 天我要為你們加以排解。”于是就判興于唐來世做某人的門婿。某人轉生到山東慶云縣,二十八歲鄉試中舉,所生一女嫻雅安靜,品貌端莊。當地的世宦貴族都爭著送聘禮來求婚,都被某人一一拒絕。后來,偶而路過臨郡,正遇上學使大人為參加官考的生員評定等級,其中考中第一名的李生――正是興于唐轉生。于是某人便邀請他到自己住的旅舍相聚,對他的款待也非常優厚。又向他打聽家中的情況,正好他還沒有配偶,于是就將自己的女兒許配李生為婚。別人都認為這是因為某人愛惜人才,而卻不知他們之間有前世的因緣。不久,李生娶了某人的女兒,夫妻生活恩愛美滿。然而這個女婿持才自傲,常常侮辱岳父,有時一年到頭也不登岳父的家門。岳父卻非常耐心地等待。后來女婿中年困頓,屢次考試都遭到失敗,岳父多方替他鉆營謀劃,終于使李生在名利場中得勝。由此,翁婿之間前嫌盡釋,感情融洽,如同父子一般。
異史氏說:“因為一次被黜,仇恨三世不能化解,怨毒之深到了如此的程度!閻羅的調解雖然很恰當;然而階下有這種冤情的人千千萬萬,如此眾多,莫非天下考官的愛婿,都是陰曹地府里那些因被黜而悲嗚呼號的冤鬼嗎?”
注釋
(1)令尹:明清指知縣。秦漢后一縣長官稱縣令,元代改稱縣尹,后因以令尹作為知縣的別稱。
(2)闈場入簾:做鄉試同考官。宋以后科舉制度,凡鄉會試同考官名簾官。見《明史·選舉志》。闈場,指鄉試,詳《陸判》“秋闈”注。入簾,指任負責閱卷的內簾官。
(3)黜落:除其名使其落榜。黜,免去。
(4)其同病死者:謂同因黜落冤憤而死者。
(5)衡文:審閱評定文章優劣。
(6)總裁:官名。明代直省主考、清代會試主司(主試官),均稱“總裁”。見梁章鉅《稱謂錄·總裁主考》。
(7)房官不薦:清科舉制度,鄉試分三場考試。頭場考畢,其試卷由外簾封送內簾后,監試請主考官升堂分卷。正主考掣房簽,副主考掣第幾束卷簽,分送各房官案前。然后分頭校閱試卷。房官可取其當意者向主考推薦,正副主考就各房薦卷批閱,再合觀二三場,互閱商校,確定取中名額。因此,房官不薦,則不能取中。房官,為鄉會試的同考官。因分房批閱考卷,故稱房考官,簡稱房官。
(8)相諉:互相推諉。
(9)例合笞:依例應受笞刑。
(10)戛然大號:指聲屈鳴冤。戛然,象聲詞。大號,大叫。
(11)抗言:高聲而言。
(12)劙(lí離)胸:剖胸剜心。劙,淺割。
(13)兵巡道:官名。明代各省下均分為數道,由按察司副使、按察僉事等官員分別巡察,稱作按察分司,有分巡道、兵巡道、兵備道等。清廢副使、金事等官,仍設分巡諸道,簡稱巡道。詳《續通志·職官·按察分司諸道》。
(14)祿:祿命。古指人一生應享祿食(俸祿)的運數。古時迷信認為人一生興衰貴賤,都是命中注定的。
(15)草菅(jiān尖)人命:謂輕易殺人。草菅,草茅,喻輕賤。《漢書·賈誼傳》:“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
(16)順天府:府名,治所在今北京市。
(17)南中:泛指我國南部,即今川黔滇一帶,也指嶺南地區。見《三國志·蜀志·劉璋傳》。
(18)慶云:縣名,今屬山東省。
(19)舉于鄉:即鄉試中舉。詳《陸判》“鄉科”注。
(20)委禽:致送訂婚采禮,謂求婚。詳《阿寶》注。
(21)臨郡:即鄰郡。臨,借作“鄰”。
(22)學使發落諸生:此指學使到任第一年,對生員進行的歲考。發落諸生,即指歲考畢,學使為試卷定等拆發,分別賞罰。諸生,明清指生員。下文“第一卷”,即一等卷中的第一名。
(23)夙因:即“宿因”,前世因緣。
(24)年歲淹蹇:中年困頓。
(25)不得售:不得售共才,意即考試不得中。售,賣,引申為考試得中。
(26)名場:爭逐功名之場,即科舉時代的考場。
(27)怨毒:怨恨。毒,痛恨。
作者簡介
蒲松齡(1640-1715),清代杰出的文學家,字留仙,一字劍臣,別號柳泉居士,世稱聊齋先生,山東淄川(今山東淄博市) 人。他出身于一個沒落的地主家庭,父親蒲槃原是一個讀書人,因在科舉上不得志,便棄儒經商,曾積累了一筆可觀的財產。等到蒲松齡成年時,家境早已衰落,生活十分貧困。蒲松齡一生熱衷功名,醉心科舉,但他除了十九歲時應童子試曾連續考中縣、府、道三個第一,補博士弟子員外,以后屢受挫折,一直郁郁不得志。他一面教書,一面應考了四十年,到七十一歲時才援例出貢,補了個歲貢生,四年后便死去了。一生中的坎坷遭遇使蒲松齡對當時政治的黑暗和科舉的弊端有了一定的認識,生活的貧困使他對廣大勞動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有了一定的了解和體會。因此,他以自己的切身感受寫了不少著作,今存除《聊齋志異》外,還有《聊齋文集》和《詩集》等。








